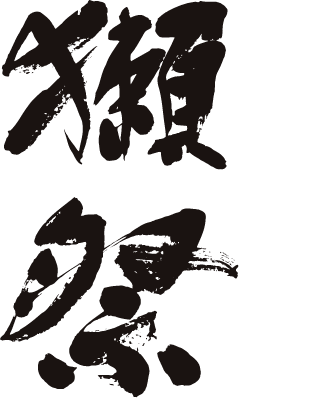獭祭的制造团队目前有220人。尽管有人认为:「透过数据化与机械化推动自动化,成功削减人力成本,建立了大量生产体制」,但这个人数对于这样的印象来说似乎太过异常。那么,问题来了:「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人?」
确实,我曾在杂志上读到,即使是年销售量是獭祭约八倍的滩地大型清酒企业,其员工数也仅为91人。而北陆地区与獭祭规模相近的地酒酒藏,也大多只有约50名左右的员工。相比之下,獭祭的人数可说是格外突出。
去年,发生了一件足以印证我们人力规模的事件。制造部门提出:「我们不需要洗米机器人了,想要报废掉它。」这台洗米机器人自八年前导入本藏以来,我们一方面持续使用完全手洗的方式,同时也将此机器人作为对照。这台机器本身几乎没有故障,在地酒业界中被视为是如神一般的优秀设备。然而,就我们洗米部门而言,它的表现仍难以达到我们的标准。
被分派至洗米作业的白米,在进行洗米前会先逐批做水分检测,并搭配精米前的各项检查,进行彻底的分析。 (我们不会因为某产地被评为特A就盲目认为它一定好。即使是同一产地的米,不同田地、不同年份的品质也都会不同。)实际上,这正是机器与人力产生差距的地方。白米的状态每一批都不同,机器无法对此迅速反应。虽然机器能严格依照规格完成吸水程序,但面对每一批米的细微差异,它却难以灵活应对。具体来说,机器的反应时间就是比人慢。而人虽然难免有些差异,但在无法进行标准化处理的情况下,反而表现更佳。
然而,使用机器的话,人手就不需要那么多。如果以洗米机器人每天的处理量来看,原本只需一人便可完成的作业,改由人工执行时,可能需要五人。仅仅是洗米这个工序,就能让人理解獭祭的制酒有多依赖人力。
其实,獭祭的酿酒之路正是经历了这样的演变。一开始,我们只是家只会酿制一般地方用酒的普通酒藏,后来开始专注于酿造纯米大吟酿,并吸引到一些颇具实力的杜氏前来支援。然而,这些杜氏虽经验丰富,却少有以理论角度分析自己的酿酒技术的习惯。
当我们在追求更高品质的纯米大吟酿过程中,对方所说的技术听起来就像神话般虚幻,我们自己也逐渐累积了经验。于是,我们开始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。更巧的是,当我开始深入参与酿酒工作时,正值数位技术蓬勃发展,设备价格也大幅下降。凭借低价数位设备,我们可以从多角度搜集数据,提升精度与实用性。结果是,过去我们还算满意的酿酒机械,在某些作业品质上已无法令人满足,反而让我们察觉到:有些工作还是得靠人来完成。这样的背景之下,从1999年我们因杜氏离开而由我与员工亲自酿酒、当时只有5位制造人员,发展到如今的220人。
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。我们在当地聘用员工,原本希望避免让他们从事麴室的深夜作业,于是引进了一款专用机器。该设备评价极高,有些使用它的酒藏甚至是新酒鉴评会的金奖常胜军。然而,来自当地的回馈却与洗米机器人如出一辙:「可以做出不错的麴,但就仅止于此」「仍感到不够满意」。最后我们也决定报废该机器,改采日本与总部相同、无法回避深夜作业的「麴箱法」来制麴。
从这一连串的故事中,或许你已经了解,这就是獭祭的风格。我们不是「守着手工制法」不放,而是「藉由技术与品质的不断进化,成长为如今的酒藏」。
今天早上的晨会中,我向大家说道:「獭祭不是靠自动化取代人力来壮大酒藏,而是透过运用数据,发挥个人力量,进而成长的。」当然,「这种方式从某个角度看,也可能是个负担,因为表面上的压力会变大。若只从压力轻重来看,交给机器做、自己当个机器的附属品确实比较轻松。」但我接着说:「但我们不认为那样就是人类的幸福,因此选择了这条路。」
我无法保证所有人都百分之百认同,但我相信大多数的同仁已逐渐认同这样的想法。獭祭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酿造出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