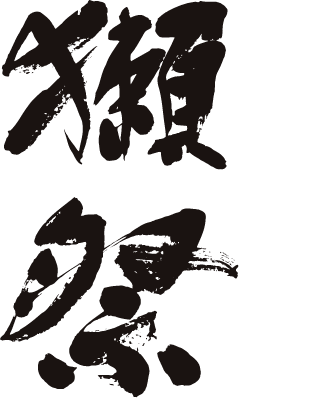獺祭的製造團隊目前有220人。儘管有人認為:「透過數據化與機械化推動自動化,成功削減人力成本,建立了大量生產體制」,但這個人數對於這樣的印象來說似乎太過異常。那麼,問題來了:「為什麼需要這麼多人?」
確實,我曾在雜誌上讀到,即使是年銷售量是獺祭約八倍的灘地大型清酒企業,其員工數也僅為91人。而北陸地區與獺祭規模相近的地酒酒藏,也大多只有約50名左右的員工。相比之下,獺祭的人數可說是格外突出。
去年,發生了一件足以印證我們人力規模的事件。製造部門提出:「我們不需要洗米機器人了,想要報廢掉它。」這台洗米機器人自八年前導入本藏以來,我們一方面持續使用完全手洗的方式,同時也將此機器人作為對照。這台機器本身幾乎沒有故障,在地酒業界中被視為是如神一般的優秀設備。然而,就我們洗米部門而言,它的表現仍難以達到我們的標準。
被分派至洗米作業的白米,在進行洗米前會先逐批做水分檢測,並搭配精米前的各項檢查,進行徹底的分析。(我們不會因為某產地被評為特A就盲目認為它一定好。即使是同一產地的米,不同田地、不同年份的品質也都會不同。)實際上,這正是機器與人力產生差距的地方。白米的狀態每一批都不同,機器無法對此迅速反應。雖然機器能嚴格依照規格完成吸水程序,但面對每一批米的細微差異,它卻難以靈活應對。具體來說,機器的反應時間就是比人慢。而人雖然難免有些差異,但在無法進行標準化處理的情況下,反而表現更佳。
然而,使用機器的話,人手就不需要那麼多。如果以洗米機器人每天的處理量來看,原本只需一人便可完成的作業,改由人工執行時,可能需要五人。僅僅是洗米這個工序,就能讓人理解獺祭的製酒有多依賴人力。
其實,獺祭的釀酒之路正是經歷了這樣的演變。一開始,我們只是家只會釀製一般地方用酒的普通酒藏,後來開始專注於釀造純米大吟釀,並吸引到一些頗具實力的杜氏前來支援。然而,這些杜氏雖經驗豐富,卻少有以理論角度分析自己的釀酒技術的習慣。
當我們在追求更高品質的純米大吟釀過程中,對方所說的技術聽起來就像神話般虛幻,我們自己也逐漸累積了經驗。於是,我們開始意識到數據的重要性。更巧的是,當我開始深入參與釀酒工作時,正值數位技術蓬勃發展,設備價格也大幅下降。憑藉低價數位設備,我們可以從多角度蒐集數據,提升精度與實用性。結果是,過去我們還算滿意的釀酒機械,在某些作業品質上已無法令人滿足,反而讓我們察覺到:有些工作還是得靠人來完成。這樣的背景之下,從1999年我們因杜氏離開而由我與員工親自釀酒、當時只有5位製造人員,發展到如今的220人。
美國也有類似的情況。我們在當地聘用員工,原本希望避免讓他們從事麴室的深夜作業,於是引進了一款專用機器。該設備評價極高,有些使用它的酒藏甚至是新酒鑑評會的金獎常勝軍。然而,來自當地的回饋卻與洗米機器人如出一轍:「可以做出不錯的麴,但就僅止於此」「仍感到不夠滿意」。最後我們也決定報廢該機器,改採日本與總部相同、無法迴避深夜作業的「麴箱法」來製麴。
從這一連串的故事中,或許你已經了解,這就是獺祭的風格。我們不是「守著手工製法」不放,而是「藉由技術與品質的不斷進化,成長為如今的酒藏」。
今天早上的晨會中,我向大家說道:「獺祭不是靠自動化取代人力來壯大酒藏,而是透過運用數據,發揮個人力量,進而成長的。」當然,「這種方式從某個角度看,也可能是個負擔,因為表面上的壓力會變大。若只從壓力輕重來看,交給機器做、自己當個機器的附屬品確實比較輕鬆。」但我接著說:「但我們不認為那樣就是人類的幸福,因此選擇了這條路。」
我無法保證所有人都百分之百認同,但我相信大多數的同仁已逐漸認同這樣的想法。獺祭就是在這樣的理念下釀造出來的。